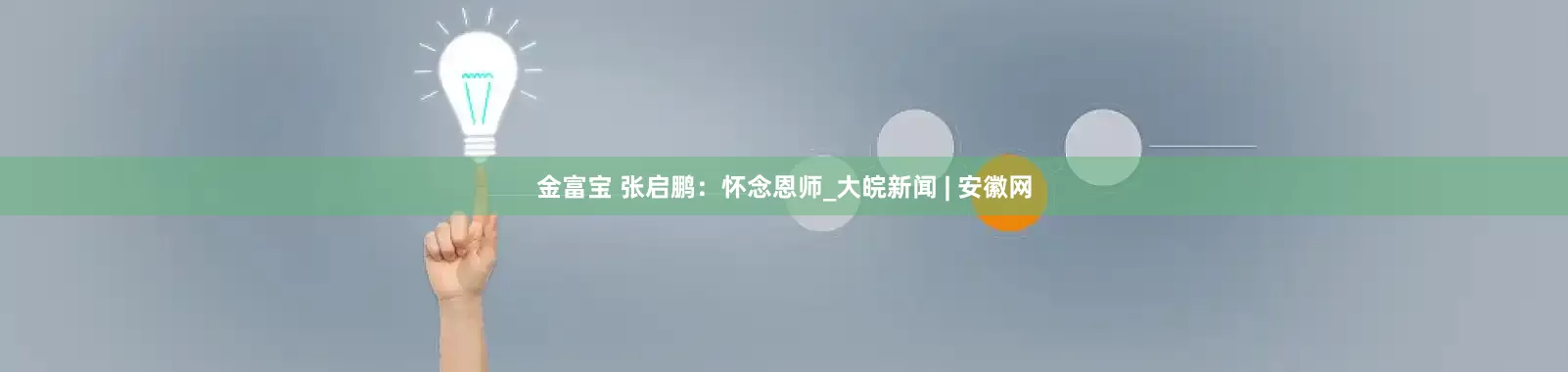
从一学弟那里得知,恩师戴恒通已于去冬仙逝,着实一惊。恩师虽年过九旬,但得益于年轻时的锻炼,身体一向硬朗,怎么突然就驾鹤西去了呢?怔怔地坐在桌前,恍惚间又看见恩师那挺拔的身影立在讲台前,藏青色中山装被风吹得微微鼓起,长长的教鞭在地图上“指点江山”,洪亮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……屈指算来,中学毕业已四十载,可恩师鬓角的白发、讲课时挥动的双臂,以及那双能洞穿人心的锐眼,从未在记忆中褪色。
恩师的家世,是一部浸着血与火的历史。其父戴蔚文,早年与戴安澜等同族有志青年投身黄埔军校,在抗战中亲历过烽火硝烟,胜利后却因积劳成疾,在恩师年少时便不幸病逝。家庭的烙印没有让恩师沉溺于过往,反而化作了他骨子里的坚韧与担当。恩师告诫我们,人要有志气,要发奋图强,“自古英雄多磨难,从来纨绔少伟男”,他常常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,鞭策我们。
1980年代的乡村中学,高中两年制,我们高一就分科,文科一个班级,理科两个班级。恩师教高一、高二两个年级地理课,更兼任高二年级班主任。在那所师资匮乏的乡村中学里,恩师像一棵擎天大树,为我们传授知识,遮挡风雨。恩师上课一般都是提前走进教室,手里捏着一叠信件,同学们都静静地坐在那里,盼望着远方的来信。恩师站在讲台上,念着信封上的名字,仅凭字迹,往往能判断出“信从何来”。小张,这是你爸爸写来的吧?小徐,这是你哥哥给你的?小王,哦,是位女同学写的,字很秀丽。小王疾步上前,接过信件,脸红彤彤的,低着头一溜烟跑回座位,引来同学们阵阵笑声。
恩师教授地理课,注重培养我们理解能力和空间想象力,首先是要吃透所有的知识点,即使是一些注释、注解等课外内容,也要求我们烂熟于胸。其次是擅长运用图表等工具,帮助我们建立空间概念,理解地理位置、地形地貌对气候、生态乃至人类活动的影响。印象最深的还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,都要熟练地画出全国铁路交通网,记得有位女同学因为完不成作业而数度崩溃大哭。
“戴老师的眼睛会说话。”这是我们私下里的玩笑话,却也是真心话。课堂上,若有同学走神,他不会厉声呵斥,只是停下讲解,目光轻轻扫过,那眼神里有威严,更有期待,走神的同学往往会红着脸挺直腰板,再也不敢懈怠。
最令恩师自豪的是,他带的班级,升学率在全县一直都名列前茅。那些年,不时有同学考上名校。尤其是恩师亲授的地理科目,同学们往往都取得优异的成绩。记得我那年高考,地理满分100分,同学小汪考了96分,我也拿了95分。多少年以后,儿子看到我当年的高考试卷,从语文、数学、英语,到历史、政治,都一一点评,指出不足。唯独对我的地理考卷,儿子翻来翻去仔细查看,钦佩不已。
恩师退休后,致力于黄埔军校学员及其亲属的联络工作,奔走海峡两岸,为民族伟大复兴,祖国和平统一,发挥余热。他晚年依旧关心教育,经常到中小学作报告,启发后生自立自强,引导他们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
恩师教给我们的,远不止书本上的知识,他用家族的故事告诉我们,什么是“家国”,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什么是“师道”,用挺直的脊梁教会我们什么是“风骨”。他像一盏油灯,在乡村教育的漫漫长夜里,照亮了我们这群农家子弟的出路,自己却在岁月里慢慢燃尽了光。
赢赢顺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